首頁>要聞>天下 天下
變遷中的鄉土中國:負面被“標題黨”無限擴大
在農業生產中,王泉林感到了極大的樂趣:“現在開著插秧機插秧,就像打游戲一樣,非常過癮。”從耕田、播種,到打藥、澆水,再到收割、晾曬,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在田里勞動。2014年,他的純收入有10多萬元。當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種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開始了自己的旅行。
對于現在的生活,他覺得很充實、很滿意。因為經營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譽度,周圍很多外出務工的人都會找到他流轉土地,“老百姓既不想賣房,也不想賣田,讓別人種著,不撂荒就行”。因為經營的規模大了,購買農資時王泉林也有了談判的能力,“現在肥料、種子都是別人送上門,找我的農資商像競標一樣。”
像王泉林這樣的農民并非個別現象,僅他所在的村民小組,還有4個種田大戶。
2000年以來,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村里的年輕人少了,村莊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村沒有了發展的空間。以往是因為務工機會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鄉村,如今全國勞動力市場形成后,農民可以自由地在城鄉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村莊里的發展空間也隨著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而逐步顯現。王泉林能夠在村莊中獲得發展機會,不正是因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務工嗎?
更關鍵的是,沒有政府和資本等外力的干預,農村自發的土地流轉形成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市場價格,這就讓留在村里的農民有了擴大農業生產的機會,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土地自發流轉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這樣無法外出務工的人也因此能夠獲得擺脫貧困的機會。
安徽農民在上海:逐夢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從未到過上海,因此對上海的農村充滿了想象。上海的繁華讓人覺得那里的農村應該比中西部的縣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發現,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敗的鄉村。
不過,與中西部破敗的農村不同,上海農村的破敗大都是因為那里的原住農民都已經進城,農村不過是大多數上海農民兒時的記憶。上海破敗的農村隱藏著許多外地農民的夢想——他們背井離鄉,在上海農村的一隅,尋找家庭發展的希望。
在上海農村的奮斗者中,來自安徽的農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區隨處可見安徽特色的餐館。除了來上海務工,還有相當大的群體在這里務農,以至于產生了與“農民工”一詞相對的“農民農”的概念。
他們大都是夫妻或舉家來到上海郊區的農村種糧或種菜。有的人實現了在這個城市戶籍的轉變,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在漂泊幾十年后回到故鄉。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眾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臨泉人,今年39歲。1994年,他大學畢業后到上海跟隨父母打拼。當時李新雨的爺爺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經親戚介紹,開始在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一個村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了30多畝地種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費倉庫,一年忙到頭,沒有雇工,每畝地純收益2000多元。過了兩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個村,在那里又租20多畝地種菜。后來發現煤球生意比較好,就向村里租了兩畝地,投資了三四萬元開了煤球廠,專門給小攤小販供應煤球。煤球廠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來,李新雨的弟弟高中畢業后從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廠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經攢下了二三百萬元,他們又借了100多萬元,向村里租了15畝土地建倉庫做物流生意。倉庫面積有7000多平方米,當時和村里的協議是倉庫15年之后歸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優先使用權,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夠凈賺四五十萬元。
2011年,倉庫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為手續不全,倉庫被定性為違章建筑,李新雨家總共得到了700多萬元的拆遷賠款——如果按照正式廠房來賠款,賠償數目則在1000萬元以上。
賠償款在家庭內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養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繼續打拼。弟弟拿到賠償款后到青浦區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萬元,還在那邊買了房子。李新雨也帶著自己那部分錢到奉賢區南橋鎮繼續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現在每個月的收入兩萬多元。但李新雨還在不斷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想重新找一個地方種菜。
編輯:鞏盼東
關鍵詞:變遷中的鄉土中國 負面 標題黨無限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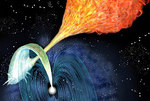 科學家破解恒星爆炸之謎
科學家破解恒星爆炸之謎 俄羅斯舉行國際煙花節 炫彩奪目美不勝收
俄羅斯舉行國際煙花節 炫彩奪目美不勝收 巴塞羅那為恐襲死難者舉行追思活動
巴塞羅那為恐襲死難者舉行追思活動 日全食將橫掃北美大陸
日全食將橫掃北美大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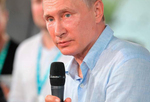 普京參加青年論壇 現場擺弄手工品“賣萌”
普京參加青年論壇 現場擺弄手工品“賣萌” 哲蚌寺展佛 拉薩雪頓節啟幕
哲蚌寺展佛 拉薩雪頓節啟幕 希臘小鎮大火持續 天空被映紅
希臘小鎮大火持續 天空被映紅 金正恩要求美國停止對朝挑釁
金正恩要求美國停止對朝挑釁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