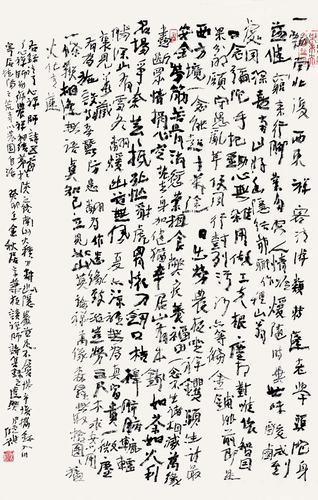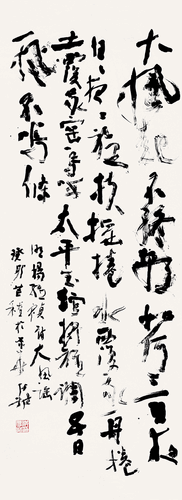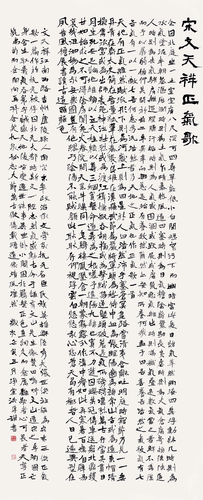首頁>書畫>畫界雜志>2024年第二期
枕思洪厚甜的書法藝術
討論洪厚甜的書法很難隨性漫談,這應是一個深刻的文化現象,應將之作一個學術化的案例加以研究。在我看來,任何賞評性的華文麗句雖可錦上添花,但無法觸及他敏感而深厚的藝術底蘊,更不可能探知他對當代書法發展的文化使命意義。作為同時代人,我們雖不宜越過歷史沉淀而將其過早地作時代使命一類的定位,但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藝術觀念與這個時代的文化藝術語境之間,實在有著太多的犬牙交錯式的互動和沖突,而且,這些互動和沖突幾乎都觸及到了中國藝術史和美學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例如,作為文本的書法藝術創作應當如何與當下具有多層次觀看需求的藝術受眾生成意義關聯、并最終確立一個普遍性的價值標準?又如,植根于文字書寫的書法藝術何以在當今時代被鮮明地劃分為專業和業余—如果“專業”一詞意味著更完善和更精準的書寫技術表達,那么技術之上的審美體驗和人文修養乃至天才式的藝術敏銳洞察力是否可以作業余和專業的二元劃分?其間是否存在德里達等人一再駁斥的“中心主義暴力”傾向?再如,作為一門生長了數千年之久的古老藝術,書法的紛繁歷時性因素導致的多元審美體驗和價值指向,是否真的可以在某一位書家筆下乃至某一件作品當中作共時性的呈現?共時性下提取而出的“線形”“線質”是否可以與“用筆”“筆法”等量齊觀?書法結字布白中的“形”是否可以與導源于西方歐氏幾何學而來的“型”這一概念混同不辨?簡單拋出以上三問,大家可以會心一笑了。理由很簡單,因為每一位執著于書法藝術的行家里手都面臨同樣的情境和問題,而洪厚甜則是拼殺在這三問中最典型者之一。以本文微薄之篇幅,根本不可能對某位藝術家的藝術風格與藝術觀念作出詳細疏解,更何況洪厚甜是位既廣博又深厚、既矛盾又圓融的書家。因此權已三問為綱,既略窺其創作旨趣,當然也順帶述及當下書法創作。
(清)了心禪師詩五首(行書)2023年-洪厚甜
先說第一問。傅山早就說過“寧丑毋媚”,意即和妍媚相比,丑乃是更高一層的審美范疇。早在先秦和古希臘圣賢們那里,對“美”的界定就頗感困難。其后,令人恐懼的“崇高”、令人捧腹的“滑稽”、乃至令人無措的“荒誕”、更無論后現代消費社會中是非難斷的“堪鄙”等等,都一一成為美學研究的重要審美范疇。即便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審美也是極為多元的存在,司空圖總結的“二十四詩品”即是一例;當代文化中,審美更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概念。多元化并非是對“美”本身的消解,而是一種對當世文化與生存體驗作日益深刻的挖掘。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很難否認藝術乃是一種為了追求美感的存在,但理應承認美的多元性,至少要接納中國傳統文化中津津樂道的天然、雄渾、悲慨、疏野等重要范疇,而非局限于了無生機的穩定秩序和矯揉造作的粉飾雕琢之中。
明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理解洪厚甜的書風追求是深植于傳統的,就是字如其名的“厚甜”二字—從樸厚、古厚、深厚、峻厚、醇厚中傳達甘甜的審美體驗,厚是形式之美,甜則是一種愉悅的精神回饋。其點畫的用筆用墨和紙張相觸相親,書家關照紙筆,紙筆回應書家,二者形成一種親厚的互動接觸,書家給予宣紙以點畫,而紙筆則回報以令人著迷的律動體驗。細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洪厚甜作書的“索取”意味更強,他近乎貪婪地借助各種手段向筆墨紙張索取那種天然律動的樂受,為了追求極致,他就必須上溯到文字最為天然的書體狀態:篆籀,他在大篆和富有篆籀筆法的六朝刻石上傾注了大量心血,這種書體用筆最近天然。蔡邕論書言“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其所謂“可象”,正是那種“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水火”“若云霧”的天然律動。因此,無論是楷書還是行草,古厚深厚的天然律動是第一位的,由此派生出了很多鬼神莫測的筆墨效應,時而汪洋恣肆,時而疏野清奇,時而如綿裹鐵,時而又如銀錐劃沙。這是得其氣而生其勢,生其勢而成其姿,成其姿而瀉其意,有此氣、勢、姿、意四者呈于一幅,觀者驚也罷,罵也好,于我何有哉?正所謂:世人欲解神仙樂,先上昆侖第一峰。
(元末明初)楊維禎《大風謠》(行書)2023年-洪厚甜
次說第二問。洪厚甜在教學時常提及“專業”一詞,言下當然頗有不滿“業余”水準的意思。關于這一概念,有古今二解。中國古代早已有從事“藝術”的專門家,有時也稱之為“方技”,二十五史中有十五部都專列了“藝術方技傳”。那些擅長星象占卜、神仙方術以及工藝和書畫的入傳者,總體地位似乎雖不算太高,但專業水準上則神乎其技,令人咋舌。唐宋以后,本算作“雜藝術”門類的書法,地位被把持權柄的文人士大夫們拔得越來越高,很多書家都進了“文苑傳”,政治地位算是升級了,而實際上書法的專業內涵也越來越豐滿了。對比于精能的技法,書法中形而上的追求越來越凸顯出來。換句話說,在唐宋以后,與文人畫同一關棙的文化現象,其實還有文人書法。書法到了歐陽修、蘇軾一班文人士大夫的眼中,日漸走向黑格爾所謂的“浪漫型藝術”—與所謂專門寫手相區別的“士意”被文人話語冠以“業余”的稱呼,形而上的“道”對形而下的“技”形成了一種話語上的壓制,當然也為“技”注入了新鮮血液。正如清人劉熙載所總結的那樣:“圣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后天,書之用也。”到了文人書法占據品評主潮的時代,漢魏晉唐不絕如縷的“筆法神授”的故事逐漸褪去靈異的光輝,被更為務實的研學圣道、修煉心性所替代了,而成為一種“筆意自得”的形態,凡人皆可得而習之。因此,書法史中“尚法”到“尚意”其實是一個文人意識充分自覺后文化思潮脫胎換骨的過程。而自清末洋務運動引進西學之后,各種公學、私學都漸以西學為尚,“專業”一詞也就成了西方學科劃分制度的內在標準。僅就“美術”而言,繪畫、雕刻、圖案工藝等都在粗泛形態上可與西方學科大致對應,書法的處境卻是有些尷尬,勉強只能在視覺類型層面劃入到“大美術”的學科范疇當中。不管借鑒了多少西方美術的所謂現代后現代藝術觀念,但書法實際的學科內涵仍舊以傳統碑帖的臨摹與理解為主—書法只是披著西方專業學科外衣的傳統藝術門類。可見,對于書法藝術來說,所謂“專業”一詞的內涵,乃是一個筑基于整個中國書法史文脈的體系性把握標準,“法”固然是“專業的”,而“意”的真正面貌,非但不是優越感滿滿的古代文人所謂的“業余”,反而更使書法具備一種充盈厚重的“專業”屬性。
洪厚甜從事書法教學正是建立在篆隸、魏碑、唐楷、行草以及各個流派書家作品通盤研究的基礎上作體系性的書法學科把握。因此,其所謂的“專業”乃是一種學科意義上的概念,包含了書法史形態的諸“法”研學與審美觀念史的諸“意”探究,并且總是以“意”貫“法”,以“法”顯“意”,為書法的體用、源流的體系性建設作出了符合當代學科標準的有益嘗試和重大貢獻。因此,字面意義上所謂的“專業”與“業余”的劃分,是權語而非實語,是圓融而非對立。在此基礎上,他運用獨立的眼光審視書體進化與書風演變的內在統一性規律,又充分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藝術創作思維特質進行書法創作表現。證道之途有理入,有行入,而兼之者才得大自在。洪氏在理法與創作上體用相成,性相互顯,自然也就消解了諸般分別知見,使其書法藝術呈現一種初見使人畏,愈玩而愈有味的妙境,此即洪氏所謂的“專業”。
(宋)文天祥《正氣歌》(楷書)2022年-洪厚甜
再說第三問。中國文字被稱為“方塊字”,這凸顯了楷書這一書體對于漢字的重大意義。洪厚甜對楷書最為注重,這當然不是緣于他擅長楷書并以楷書成名—這是果而不是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從書體進化和書風演變的雙重角度加以深入研究:楷書是建立在篆隸線質的基礎上,以及行草書的筆勢貫通前提下的一種狀態存在,即楷書包含了篆隸之“質”和行草之“勢”。他決不會認為楷書是什么圣賢突發奇想而推行的文字書寫規范,而認為楷書應是漢字合規律合歷史的必然發展結果。這一識見與文字學大家裘錫圭先生的論斷不謀而合,裘氏在《文字學概要》中曾明言:“我們簡直可以把早期的楷書看作早期行書的一個分支。”我們知道,在書體發生隸變這一關鍵期,出于快速便捷書寫的章草字體也同時流行起來。無論漢隸還是章草都接續了篆書。一方面,古老的篆籀雖有書寫上的繁瑣性,但禮制的強大文化慣性使得篆書成為典則;而另一方面,社會發展導致的對便捷實用性書體的迫切需求,又使得當時流行的八分漢隸必須增加書寫速度。在此文化與功利的雙重作用下,既有篆隸的典雅之質,又得章草便捷之勢的新書體必然要應運而生。在歷史上,人們一時間甚至都無法為這種既隸又草的新書體確切命名,正是出于這種新書體的高度復合特質。從這一角度來看,洪厚甜對楷書的定義無疑是以書法家的藝術直覺力切合了文字學家的學術洞察力。
然而,對于楷書這一新體來說,視覺形態上畢竟有了全新的改變,傳統篆隸中“引”的單純筆法被快速筆勢牽帶出的豐富“點畫”所替代了。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六朝書家對“永字八法”的熱烈討論。為了正本清源闡述篆隸章草對楷書書體的生成作用,洪厚甜論書頗為大膽地選擇了一個非常西方化的美術概念:線條—以及由之派生出的線形和線質等概念。從源頭講,作為幾何學術語的“線”與中國書法的“筆”二者在文化思維層面和實際運用上皆有著本質的差異;洪氏早年在中國美院接受了書法視覺形態剖析的相關訓練也對其論書術語形成了一定影響。但這并不妨礙他在創作中對傳統筆法的有效運用。莊子云:名者實之賓也。洪氏所謂的“線”,并非幾何學意義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實有其氣、實有其勢、實有其姿、實有其力、實有其意的“筆”。從學理上說,幾何學意義上的點、線、面,因其根本的抽象性只能生成“型”;而元氣論哲思下的用筆,卻必然會呈現出造化天地的“形”。而且,此處的“形”實是包含了“象”的概念,成為一種貫通書家、作品、世界以及受眾的復合形象。關于這一點,只要看一下他的實際作品便不難理解。他寫大篆,注重傳達用筆的古奧奇崛氣象,寫漢隸,突出了排宕闊大的氣勢,寫《好大王碑》,洋溢著天然自得的氣韻,寫褚遂良楷書,夸張出質樸凝重的氣力。“線”和“型”這些概念,只在表述創作策略的方便上發揮其功能。每一位書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線條的方圓、粗細、長短、輕重,型的大小、聚散、開合、主次等等主客二分思維下的技法形式,只不過是渡河之筏、得魚之筌,決不可執相而求。誠然,洪厚甜具有極為豐富的創作經驗和多重的表現手段,但這都是由性顯相。非要對所謂的“性”加以說明—這里我不想說得太玄—毋寧說是對中國傳統思維和藝術觀念的深刻理解。洪氏的杰出之處,正在于他從中華思想史層面高屋建瓴地把握書法。可以說,無論寫哪一種書體或書風,他都在努力復現整部的書法史,都在試圖呈現整個漢字文脈,都在不斷回味中華歷史中那份歷久彌新的精神價值體驗。
書雖小道,其旨為大。從美學層面觀察洪厚甜書法藝術的意義,實際上早已超越書法本身,而觸及了到藝術創作與接受、文化傳承與創新以及東方與西方觀念交融等諸多宏大命題。本文正是從這一主旨出發,以寥寥數語管窺洪厚甜的藝術。
2022、 8、30于八大處
洪厚甜
1963年生于四川什邡。師從李良棟、蒲宏湘、張海、陳振濂、何應輝、曾來德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黨支部書記、副所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美術院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四、五、六、七、八屆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院研究員。
致力于書法創作和書法教育的實踐和探索四十余年。中國美術館舉辦“凈堂墨華—洪厚甜書法藝術展”,中國國家畫院舉辦“一畫開天—洪厚甜書法藝術展”。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全國展和文化和旅游部中國藝術節書法篆刻優秀作品展評委。先后出版《凈堂藝跡》《凈堂擬古—洪厚甜臨古法帖系列》《洪厚甜楷書碑版系列》《書法的技法與觀念十講》《洪厚甜書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等二十余種。
責任編輯:楊文軍
版面設計:湯煒
編輯:畫界 邢志敏